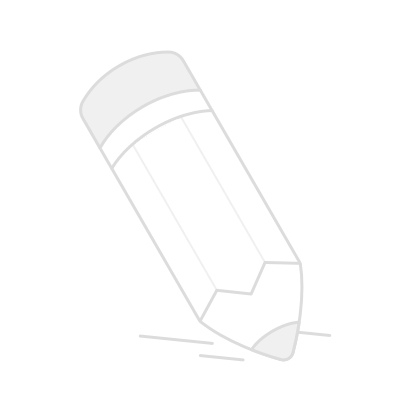各式各样榜单是每年年终电影文化中最生龙活虎的部分,得益于今天社交网络开放而又民主的设计理念,榜单不再是传统电影媒体的垄断话语。在豆瓣,在微博,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发布自己的年终榜单。对于很多影迷,列榜单或许仅仅是其一年迷影生活的整理和总结,是与ta的朋友分享和讨论过去一年来的观影收获。但,一份榜单,无论它出自谁之手,又带着怎样初衷和动机,它都会被迅速纳入到一个话语体系里。不可避免地是,只要是榜单,它就一定是“挑选”和“评价”,它也就一定代表着一种“意见”,一种“立场”,乃至是深思熟虑的一种“美学”倾向,甚或是在回答“电影是什么?”这样一个本体论问题。既然,关于某部电影,大家的评价就可能会是南辕北辙,七嘴八舌的;那么弥漫在榜单背后的恩怨情仇便不难想象了。
在关乎“审美趣味”这个核心概念最真知灼见的形而上反思里,康德最具洞察地向后人表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,任何审美趣味表面上都是个体性的,特异性的,但在其最根基处却必然要求着一种最先天的普遍性。把这个道理翻译成人话就是,当你判断一部电影是好电影时,你也最本能要求所有人都认同这是一部好电影。当然,康德当年举例子时候,常常指的是一朵花,而电影显然是太过于复杂的审美判断,掺杂了太多文化和非文化因素。但康德教诲之所以在今天依然成立,正是因为,当我们面临审美分歧时候,今天人们仍旧在互联网上以温和(或粗鲁)的方式试图说服(或攻击)他人。同样的,任何认为审美都只是一种个人判断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品味,因此不要较真,没必要说服对方的观影者,以我之见,也没必要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电影判断。因为,“判断”只可能是公共的,它先天包含着普遍性要求,很多人所谓的私人“判断”,只不过是无足挂齿的私人“感想”罢了。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我以为榜单本身——十部、二十部、一百部电影的名字是无用的,这最多是一个姿态,一个名头,一个聚拢电影资源的集合名。而真正有价值是,榜单背后所必然蕴含着的“道理”,是每个人捍卫自己审美判断的趣味和立场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「深焦」编辑部决定在2015年最后几天里推送这份策划。它将着眼于“为什么”,而不是“是什么”。它不甘心像传播一份噱头资讯一样,告诉你全世界最具理论素养的杂志,又做出了怎样“高冷”和的选择,而是试图向每一位读者展示,《电影手册》每一个选择背后,有其固有的理论基础和美学立场。作为全世界对整个世界电影史影响力最大的杂志,它们的选择不仅仅是“哗众取宠”,或者至少是在其自身逻辑和一致性下“哗众取宠”。
在和babydog交流和学习过程里,他始终有一个观点是我想在此最后提及的。因为他曾反复质问同时也是自我质问,中国乃至亚洲的影迷到底要跟在《电影手册》这样的杂志屁股后面多少年,什么时候我们才可能有自己的话语,自己的判断,不需要在看完电影之后,去看手册怎么评价,去翻译手册的文章?对于这个问题,事实上,国内早有两类反应:当一批影迷拉着《电影手册》这个“权威”的“大旗”,褒扬或贬低一个电影时;同样也有一批影迷自信地宣称,手册不过是一个仰仗着新浪潮遗产,并且把家产败落得差不多的过时杂志。尤其是考虑到这二十年来,它几度易手,甚至面临生存危机。我想,在这里,以我个人亲身经历来尝试着对这个问题和现象作出我个人回应——
但凡真的读过《电影手册》的人都知道,这确实是一本很高难度杂志。这种高难度首先在于它的法语很难,大量生词和复杂长难句,难到我们「深焦」里法盟老师理解和翻译起来也是捉襟见肘;其次,手册的确是一本有其自身理论传统和美学趣味杂志,它对电影有一套独特的但绝对是自圆其说的评价标准。这种标准有时候会导向一种与大家常识偏差非常大的评价,比如今年手册极度厌恶金棕榈《流浪的迪潘》,索伦蒂诺《年轻气盛》,罗伊·安德森《寒枝雀静》,对评价颇高的《索尔之子》也只是冷眼相对,反倒是热烈拥抱起名不见经传的《气味相投》和《桑格莉之夏》。但很多时候,不得不佩服是,我周围凡是阅读了对《迪潘》批评朋友,几乎都一边倒赞同手册非凡洞察力;但另一些判断,或会因为手册而改变看法或也是看完以后也嗤之以鼻。但有一点恐怕是大家共识,手册是一本讲道理杂志,即使作者的出发点和知识背景可能会与读者完全不同。说实话,与手册批评的深度和独立性相比,法国另一本历史悠久知名杂志《正片》则逊色不少,大多数英美主流电影刊物也难以望其项背。虽然国内已经有一些不错的影评人,但要持续性,稳定地达到手册编辑高度,还仍有一段距离。在这个意义上,我仍旧觉得,翻译乃至参考《电影手册》批评是我个人理解和学习电影的一种方式。
对于绝大多数国人,因为语言缘故,《电影手册》在今天的真正影响力只停留在一张有着十个电影名字的榜单上。正是因此,我们「深焦」必须要做这样一件事,而且也会一直做下去,就是去啃这些硬骨头,去翻译那些有真知灼见的好文章(《电影手册》的,《正片》的,《视与听》的……)。虽然,它只是二手的,但我们仍希望能帮助我们读者在这种阅读、反思和观影的反复过程中不断进步,而不是空有一个逼格姿态,把电影品味变成个人身份的装饰品;而是不断去反问自己,电影究竟是什么?电影和生活有着怎样的关系?我们又为什么要看电影呢?正如《电影手册》主编Stéphane提的那个问题“占据我们如此多时间的电影世界能否反哺我们的生活呢?”我是相信的,而且,何止是“反哺”,杨德昌已经给出了最好的答案,“电影的发明使我们的人生延长了三倍”!
写于电影发明一百二十周年。
——Peter Cat